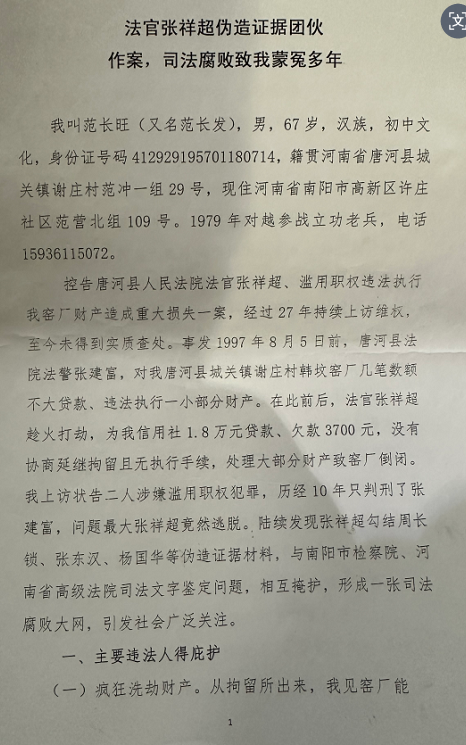内容提要:跨学科性被视为比较教育的本质属性之一,但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跨学科原因以及跨学科方法在比较教育中的应用都存在含混不清之处。这使得曾经构建科学比较教育学的跨学科性逐渐成为人们质疑比较教育存在合理性的一个导火索。本文在考察比较教育跨学科原因的基础上,探讨了当前比较教育跨学科研究存在的若干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比较教育的有限开放。
关 键 词:比较教育 跨学科性 跨学科限度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5)09~0022~08
19世纪末期,社会科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开始出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萨德勒(Michael Sadler)提出“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的比较教育思想。从此,比较教育研究开始广泛地关注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对他国教育作出合理解释。经过康德尔(Isaac L.Kandel)、汉斯(Nicholas Hans)、安德森(C.Arnold Anderson)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比较教育中的跨学科初现雏形。“二战”后,由于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跨学科也逐渐摆脱了过去的“隐结构”状态,通过贝雷迪(George Z.F.Bereday)的“四步法”被明确提出来。此后,随着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蓬勃发展,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也进一步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跨学科方法在形塑科学比较教育学的同时,也带来了比较教育的学科危机。法国学者黎成魁()认为,正是由于比较教育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因而不能称之为一个学科,只能作为一个领域。[1]甚至所有与教育相关的问题,只要涉及国别,就可以称之为比较教育研究,它没有一个中心,关涉的课题繁多,而课题之间似乎又没有多大联系。[2]跨学科被滥用,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究其根源,还是比较教育研究缺乏限度规范,将跨学科性错误地理解为无限制的开放性。因此,本文在对比较教育的跨学科性进行澄清的基础上,讨论比较教育跨学科的限度,探讨如何实现比较教育累积式的可持续发展。
一、比较教育研究跨学科性的原因分析
(一)比较教育“传统二元性”存在跨学科的共性
在比较教育的发展史上,存在过两种主要的模式——“德国模式”和“英国模式”。[3]“德国模式”是德国以及欧洲中部和东部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教育的一个明显特色,即将比较教育作为具有哲学倾向的普通教育学(General Pedagogy)的附属。这也与朱利安所倡导的比较教育相一致,即通过收集准确理想的“关于欧洲国家目前情况的教育比较表”,“使之相互联系、便于比较,从而演绎出一些原则和明确的法则,以便使教育成为近乎实证的科学”。[4]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奥斯卡·安维利尔(Oskar Anweiler)对比较教育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它是与历史学和社会学关系密切的“交叉部门的领域”。[5]这为比较教育向外部学科开放其边界打下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摒弃了它作为普通教育学的附属的传统。而“英国模式”则从未热衷于建构一个普通教育学,它更倾向于单一教育学科的制度化和结构化。在这种模式下,离开任何致力于“问题”的讨论,比较教育都有可能被取代。[6]这种围绕问题为中心的模式,也致使比较教育的方法不囿于某一学科的范围,而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展研究。
不过随着跨学科研究在英国,甚至全欧洲、全世界的增长,这一“传统二元性”变得越来越过时。但是与普通教育学及其他临近学科的关系,体现了比较教育的发展越来越摆脱了普通教育学的束缚,成为了一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学科。
(二)比较教育学科的知识特征与制度结构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一词,主要是指科学研究群体所公认的学科信念、基本概念、原理、方法以及工具等。[7]学科发展既是知识体系的重建过程,也是学科文化的发展过程;既是解释逻辑的更换,也是学术共同体中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语言规则、实践标准等的“跃迁”。可以认为,一个学科基本的性质包括了一个认识论的尺度与一个社会历史学的尺度。[8]前者关涉学科的知识特征,即知识实质与真理要求,它倾向于展现永恒的、普遍的和必要的特征;后者关涉学科的制度结构,即社会和政治制度中知识实质的具体化——将知识内容的体现予以政治制度化,它倾向于展现变化的、特别的和偶然的特征。
1.比较教育学科知识特征
比彻(Tony Becher)按照学科知识特征,将学科分为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应用软科学四种类型。[9]硬科学所对应的严密知识的范围一般比较清晰,研究的问题比较确定和狭窄,注重定量的问题,一般由因果关系命题、普遍的结论和普遍法则组成结构完善的理论。软科学所对应的非严密知识的范围比较宽泛,界限不清晰,问题的定义也不特别严格,理论结构也相对不确定,注重定性和特殊性的分析。比彻将包括教育学在内的应用社会科学归入应用软科学类别。
一项2004年开展的针对美国国际与比较教育学会(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duction Society,简称CIES)成员的调查研究显示,比较教育学者最为关注的学科领域依次是:教育规划与政策、社会学、经济学、国际教育/贸易、比较国际教育、理论、人类学、区域研究、行政/管理、高等教育、教育史、语言政策等。[10]比较教育中最频繁出现的主题依次是:全球化、教育性别、教育与发展、教育平等、多元文化、种族、方法论/认识论、改变与改革、经济、小额信贷、私有化、经济资助与发展、政策/政治/规划等。[11]这表明比较教育符合软科学知识的研究主题范围宽泛、界定不清晰等特征。而松散的、非限定性的软学科,其研究更易发生跨学科的行为。
2.比较教育学科制度结构
学科的制度结构并不是局限在正式的知识和位于院系内部的学术结构,也包含学术团体和其他形式的学术网,例如学术刊物、会议及学会的信息等。[12]对CIES成员的调查数据显示,比较教育成员构成具有与生俱来的多重性,开放的准入标准与相对年轻化的人才构成都表明CIES成员在专业认同度上较为薄弱,人员变更剧烈。[13]这些因素最终导致比较教育组织在边界连续性、研究成果持续积累、历史发展意识等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
学科知识特征与学科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交织、不可分割的。其关系的流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渗透的,学科知识特征会影响学科制度结构,软性知识相对应的学术组织关系较为松散;同时,学科知识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化地建构的。可以说,比较教育的跨学科性不仅是由其知识特征决定的,也是比较教育学科共同体在长期学术实践过程中共同建构的。
(三)科学比较教育学建立的需要
在欧洲比较教育历史上,比较教育作为一个学术学科出现于伦敦。[14]通过萨德勒提出“民族性”概念以及研究校外事情的主张,打破了过去就教育论教育的情况。这为以历史法为主要特点的因素分析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使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开始形成。
从此,比较教育的目的论开始从借鉴转向依据其对其他国家以往以及类似经验的观察,对某个国家教育制度是否能取得成功作出预测。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在移植其他国家的任何经验之前,都要经过一个预备阶段。在这个预备阶段中,比较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研究与教育有能动关系的各种社会因素,揭示构成教育制度基础无形的精神和文化力量,也就是民族性。从康德尔到汉斯,都认为教育是民族性影响的产物,教育制度是植根于历史的,因此比较教育要采用历史的方法来分析形成教育制度的因素。在汉斯看来,历史法,在其具体实施中就是进行因素分析,也就是说,因素分析是历史法的具体手段。[15]这与萨德勒和康德尔的比较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因素分析法则是后来贝雷迪在比较“四步法”中所倡导的对教育现象做多学科分析的雏形,这也是比较教育跨学科性的起源。[16]
(四)社会科学发展对跨学科方法的推动,以及对比较教育的冲击
19世纪晚期起,社会科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现以后,一个逐渐分化,同时又逐渐跨学科整合的相互作用的运动就发生了。与工业化保持密切关系的专门化和专业化,加速了一个又一个社会科学学科的建立。但是正如美国社会学学会创始人之一的阿尔比恩·斯莫(Albion Small)所言,“专门科学,无论是物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条分化的科学道路。在这条分化道路上,由于缺乏一致性,科学变得不能令人信服。这正如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当时的科学具有广度而缺乏深度,但现在虽有深度却又缺乏广度”。[17]基于这样的原因,以美国芝加哥大学奥托·诺伊拉特(Otto Neurath)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为通过跨学科整合以及社会科学的聚合,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努力。[18]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带来单一学科迅速膨胀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推动了跨学科方法的发展。比较教育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来自不同教育和学科背景的比较教育学者,在保有自己本身学科的同时,还将当时该学科流行的方法引入了比较教育研究。
不过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术机构的“显结构”一直被学科所主宰,跨学科处于一种“隐结构”状态。直到“二战”后,各国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和综合国力的需要,开始加大对应用科学的投入,通过政府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以任务导向的项目形式来促进科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工作。因而,20世纪后半期,随着异质性、杂糅性、复合性、跨学科等成为知识的显著特征,“显结构”与“隐结构”之间的平衡也发生了变化。[19]这也影响到了比较教育方法论的转变。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比较教育开始转向比较与国际教育,成员由多学科、跨国家和跨文化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所构成。波斯东认为,从这一时期开始,“正统”学科开始让位于包含了一切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异端邪说”。历史作为教育比较研究的唯一合法的学科基础地位被抛弃,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开始出现巨大转向。[20]
以上从比较教育的“传统二元性”、学科知识特征与制度结构、学科发展需要等角度探讨了跨学科性作为比较教育的一个本质属性的原因。在比较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跨学科性逐渐得到广大比较教育学者的认可。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由于跨学科性又存在很多含混不清之处,这又影响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积累与可持续发展。
二、跨学科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纵观比较教育发展史可以发现,尽管跨学科获得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但是不同时代的比较教育学家对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即便是同时代的比较教育学家,由于受到自身人生经历和学术训练的影响,对比较教育要跨哪些学科、如何跨学科等重要问题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卡扎米亚斯(Andreas M.Kazamias)主张以历史和社会科学综合的方法研究比较教育;安德森认为比较教育本质上是社会学的分支;贝雷迪主张将若干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的学科聚集起来,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运用于比较研究;霍姆斯(Brian Holmes)更倾向于本质上从具有详尽、有效的物理科学方法论视角出发研究比较教育。
此外,曾经的专业训练和职业经历也使得学者们在从事比较教育研究时,仍受到原来学科流行趋势、方法的引导,并将这些趋势、方法带入比较教育研究。例如,20世纪50年代,安德森和福斯特(Philip Foster)追随美国当时最盛行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研究教育内部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时,通过孤立和控制变量的方法,谨慎地收集相关数据,以经验为主来检验一个具有共变特征的假说,强调测量与定量的技术,以及通过消除研究者主观观点、信念和偏见,使研究尽量客观化。[21]
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跨学科充满了随意性和滞后性。跨哪些学科、怎么跨,跟学者自身经验有关,且追随着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脚步亦步亦趋的发展。对跨学科方法的不当应用,也为比较教育研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不良影响,并最终导致曾经形塑科学比较教育学的跨学科逐渐演变为比较教育学科危机的一个诱因,成为人们指责比较教育不是一个学科的根源。
(一)粗放的跨学科研究导致比较教育知识难以积累
1974年,缪达尔(Karl Gunnar Myrdal)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认为,“他们完成了重要的跨学科工作,他们发现了新的、独创的方法来提出问题,他们的研究有可能改变我们社会盛行的组织、制度、法律环境。但是由于挑战了学科的传统,从而使得他们是有争议的”。[22]学科将世界划分为碎片的形式,这样有助于知识的积累,但是也阻碍了新知识的创造。跨学科研究通过“将知识互相依存的部分整合成协调的关系”,而“将数个(至少3个)学科联合起来”,使知识重新回复到一起,[23]从而为人们提供一个机会,通过新的视角,创造新的方法和知识。
但是比较教育中的跨学科在新方法、知识的创造上却长期处于滞后的情况,且随着主流社会科学学科方法的变迁而改变。卡扎米亚斯因此将比较教育称为“易变的知识”,[24]也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没有根的。[25]这也导致比较教育过于直接地回应了学科流行的改变,而抛弃学科过去的实践,从而最终影响了学科的“累积式前进”,致使长期停留在乡村性质的研究水平。[26]此外,这种粗放式的跨学科研究所取得的研究结果,其科学性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在中国,特别是在其他教育学科普遍将视野扩大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地区之后,我国比较教育不加限制的选题方式使得它与教育其他学科出现了严重的重合,却并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这无疑加重了人们对于比较教育存在必要性的疑虑。
(二)跨学科的合作停留在较低水平
除了单个学者从事的跨学科研究,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跨学科还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即团队式的跨学科合作。西班牙学者何塞·加西多认为,在大量的比较研究中,团队协作是必不可少的,比较教育学者充当着将众多专家的分析疏通和糅合成一份能自圆其说的整体报告的作用。[27]但是实际情况却不能令人满意,“在组织了多次会谈之后,我们发现,只要事先掌握足够多的关于一个专家专业性质的信息,就可以很好地预测能从任一专家那里得到的答案。每一个专家都在给定的环境中找到对他而言熟悉的环境,尽管他可能也承认他的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中的重要因素,但是,他的建议往往潜在着‘优先考虑我的因素,然后才是其他的’这样的说法”。[28]所以,即便组成了合作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松散的。[29]跨学科研究的优越性和创造性并不能表现出来,跨学科合作往往停留在较低的水平。
(三)比较教育的定义难以获得普遍认可
建构主义认为,“由于感官所接受知识的输入,是选择性的注意,所以观察本身是包含着理论因素的;如果观察受到理论的左右,那么,观察的性质就受到先在理论性质的支配”。[30]因此,比较教育学者曾经的生活经验和学术训练,不仅影响了他们对于跨学科的选择,也会进一步影响到他们的比较教育观。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尽管因为比较教育而聚集在了一起,但他们各自从自己原本学科的基础上思考比较教育的问题,最终导致了任一比较教育定义都难以获得普遍认可。
康德尔和埃德蒙·金(Edmund King)都曾谈到,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应该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而定。比较教育学者不同的比较教育观,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们对跨学科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应用获得认同。而无法取得普遍认可的定义,也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爆发比较教育学科危机的导火索。
(四)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界限模糊
贝雷迪曾经对跨学科的问题进行过认真细致的考察,“比较教育和其他基础(学科)——教育史、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在谈到比较教育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的时候,他曾经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就研究学术科目的训练可以将人塑造成白领这个问题上,应该属于教育社会学还是比较教育学?还是二者皆有?还是说,当我们提到“在苏联、印度尼西亚、日本和一些其他国家获得的证据证明,学术科目的训练将使人成为白领”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跨越了从社会学到比较教育的边界?当加上国别和地域的限制时,与教育有关的任何问题就可以纳入比较教育的范围吗?[31]这个问题直到今日,依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从我们专业刊物刊登的文章,到学会提交的论文,甚至博士选题都是五花八门。我们甚至很难界定哪些选题是不属于比较教育的范围的。界限模糊也导致了比较教育人才培养陷入矛盾的境地。
(五)比较教育现行体制难以培养需要的跨学科人才
大学是以学科为单元、以教学和研究为基本行为的学术组织系统。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导致了知识的专门化趋势,与之相对的是学科的不断分化和专门学术领域的形成与细分,每个单独的学科都在发展自己的一套概念框架、理论和方法体系。学科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说它构成了“第一原理”,知识的专业化是“构成其他一切的基石”。[32]跨学科组织和机构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发展相对缓慢,跨学科人才的培养举步维艰。
此外,比较教育的跨学科人才培养也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在美国比较教育发展史上,曾经将比较教育人才培养限定为“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博士学位往往授予那些具有宽广视野的人,但这造成了他们在每一门学科中都缺乏应有的深度。为了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20世纪中叶,美国比较教育学界开展了一项运动,主张在一个领域和学科的范围内去训练博士研究生。只有在完成博士训练之后,再以追加或补充的方式,鼓励他们在其他学科和地理领域中扩大研究的活动范围。但是这一运动暗含着比较只被工作中的学者所采用,而并不被博士研究生所尝试。[33]这自然激起了人们的反对,但也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于比较教育持续依靠其他社会科学,而找不到一个“停泊处”的担忧。“什么是比较教育的基本工具?什么是我们应该使用的基本学科?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和哲学?还是这些的联合?人们对于比较教育是一个几乎任意所有方法的聚合越来越感到不满”。[34]这一问题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比较教育研究需要跨学科人才,但是现行培养体制却难以培养这种具有跨学科能力的学生。
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跨学科性,由于其随意性与滞后性所导致的跨学科水平较低,合作停留在形式上,学科定义不明确,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界限模糊,以及随之而来的培养体制缺陷等问题。这些问题彼此相互作用,互相影响。没有高水平、有序的跨学科研究,学科知识就无法得到有效积累,最终必然导致学科发展受限等一系列问题。以上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比较教育的跨学科缺乏应有的规范。
三、比较教育——有限的开放
(一)学科具有限制性
英文“学科”(discipline)一词,从词源上讲,有信徒、门徒、追随者的意思。在语言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用来指称“学者和信徒的训练,即通过指导与练习,而拥有同样的适当的举止和行为”。“学科”同时具有“用于规范举止的规则系统”,以及“用以维持那些处于控制和命令下的人们的秩序”或“一个训练的环境”的意思。本质上,“学科”一词具有“纠正”或“惩戒、责罚”,以维持“秩序”和“适当的举止、行为”的内涵。学科通过发展自己的一般概念框架、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将所有最终的分析都建立在其不言而喻的哲学假设之上,从而形成对世界的不同理解。每一个学科共同体的成员都内在地、部分地分享他们自己的一套独一无二的世界观。反之,就会受到惩罚,如作品不能得到发表,或者拿不到学位等。因而,学科具有两种属性,即生产性和限制性。在学院中,它生产、积累知识,加深着人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理解,同时也限制着学科成员的世界观。
尽管仍有很多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对跨学科性的讨论也源于“领域”抑或“学科”的争论。[35]但是,正如王英杰会长在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第16届年会闭幕式上所讲的,“比较教育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因此,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将比较教育发展成为一个有自己概念框架、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对所有成员都有一定约束力,有自己独一无二世界观的学科而努力。这也是比较教育摆脱方法论的滞后性,提高研究质量,实现学科累积式发展的可能路径。
(二)教育是有限的,比较教育也是有限的
比较教育似乎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与教育有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纳入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围,成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但“万能的”比较教育却常常因为其科学性和与其他学科研究对象的重合,而被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
比较教育研究的是与教育相关的问题,而教育本身是有限的。当今社会,尽管教育被广泛地用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教育却并不总是有效的。教育发挥其功能、作用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它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有限的条件下,实现特定手段的有效性。[36]由于环境和人的差异,同样的教育手段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在此处可以成功的教育手段,到彼处就有可能失败。如果对这个环境和条件判断误判或忽视,就会给决策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及整个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伤害。
比较教育在不断科学化、理论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研究结果的有限性,而将对前提条件的探讨置于重要位置。比较教育对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的研究,由于该国和地区环境、传统、宗教、文化、国民性等的差异,得到的都只是有限条件下的待检验的理论假设。只有将其与不同区域教育研究得出的结论进行比较,才能将这一理论假设逐渐证实或证伪,从而抽象出一般性的理论。只有一般性的理论才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但是这里所说的一般性理论绝不是科学的尽头,或绝对的真理。卡尔·波普在其经典论著《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指出,“科学不是一个确定的或既成的陈述系统,它也不是一个朝着一个终极状态前进的系统。我们的科学不是绝对的知识:它决不能自称已达到真理,甚或像概率一样的真理的替代物”。[37]正因为科学不是绝对的真理,通过比较教育研究得到的一般性理论,在指导实践过程中,应当尤其重视该理论应用的原始条件和现实条件。因此,比较教育的限定条件包含两方面的内涵:第一,从一国或地区得出的区域教育研究结论,只是基于这一区域前提条件的理论假设,只有通过与其他区域教育研究结论进行比较,才能检验理论效力,不断完善其成立的前提条件。第二,在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既不能忽视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也不能忽视实施地当地的现实条件。否则比较教育研究成果很难具有指导实践的效力。
(三)比较教育所跨学科是有限的
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一书中将知识生产模式划分为模式1和模式2两种,其中模式2被认为是当代知识生产模式,具有跨学科、异质性等特征。[38]由此不难理解作为当代知识生产新模式的跨学科研究在当前各学科、领域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比较教育的跨学科性由于其学科发展的内部逻辑与外部力量的影响,有其自身的限定性。
库克(Bradley J.Cook)等人的调查研究显示,在参与调查的75个比较教育组织的419名成员中,有15.5%的人在比较教育学上获得他们的最高学位;其次是国际教育,占8.2%;教育规划(educational planning),占5.8%;而剩余的70.5%则来自于诸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此外,通过对比较教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三本杂志:《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比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和《教育发展国际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的引文分析,发现所有的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39]从比较教育组织成员学科构成到比较教育相关杂志引文分析,不难看出比较教育学术共同体构成及研究活动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但同时又相对稳定地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关系密切。
斯米尔诺夫(Smirnov,S.N.)指出,跨学科有两个影响因素——历史因素和知识结构的新进展。[40]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与教育学有着传统的“姻亲关系”,关涉与比较教育相关的各种因素,彼此间也存在专业层面上的公共性。这是在所跨学科上比较教育研究的限定性,但这并不表示比较教育必然地要跨上述几个学科。除了上述传统上与比较教育学有“姻亲关系”的学科外,比较教育研究所跨学科还受到知识结构新进展的影响,新的现实需求会把原本彼此间关系并不紧密的学科联系在一起,形成另一种“姻亲关系”,以解决复杂问题。例如,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受信息社会、全球化、知识经济、后殖民主义等新形势的刺激,比较教育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全球排行榜、大数据和教育研究方式的国际转移。其中,由于基于证据的教育政策借鉴受到来自自然科学研究和医学领域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简称RCTs)模型所转化而来的认识论逻辑假设的支持,基于大数据的国际比较研究与解释,正受到世界各国教育政策制定者的关注。[41]历史因素与知识结构新进展的影响,使得比较教育的跨学科性是有限的,同时又是不断发展的,如同比较教育这个学科一样,是开放的,同时又是限制的。
四、结语
学科拥有生产性和限制性,同时又会被推向它所限制思考的观点和看法。所以,比较教育一方面需要在持有学科边界的基础上,对有限问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突破学科限制,探索新的学科生长点。学术研究最理想的状态是保持一种介于“学科”与“反学科”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维持这种紧张关系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深入地沉浸于一门学科之中,并联合来自本学科、其他发达学科中恒定的知识。[42]因而,比较教育需要对教育相关的问题进行有限制的跨学科研究,关注传统学科领域,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探求一般教育理论,以提供更可信赖的政策借鉴。
参考文献:
[1][法]黎成魁.比较教育[A].周晓霞译.赵中建,顾建民.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4.
[2][美]盖尔·P.凯利.比较教育的论争与趋势[J].郑桂泉译.比较教育研究,1992,(5):29-34.
[3][5][6][14]Wolfgang Mitter.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Europe[A].Robert Cowen,Andreas M.Kazamias.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C].Dordrecht:Springer,2009.87-99.
[4][15][16]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23-24,90,108.
[7][18][28]Raymond C.Miller.Varieties of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A 1981 Overview[J].Issues in Integrative Studies,1982,(1):1-37.
[8][12]Maria Manzon.Comparative Educ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a Field[M].Hong Kong: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2011.16,222.
[9][英]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
[10][11][13][39]Bradley J.Cook,Steven J.Hite,Erwin H.Epstein.Discerning Trends,Contours,and Boundari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A Survey of Comparativists and Their Literature[J].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2004,48(2):123-149.
[17][24]Andreas M.Kazamias.Re-inventing the Historical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Reflections on a Protean Episteme by a Contemporary Player[J].Comparative Education,37(4):439-449.
[19]唐磊.理解跨学科研究:从概念到进路[J].国外社会科学,2011,(2):89-98.
[20]Gita Steiner-Khmnsi.The International Race over the Patronage of the South: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J].Current Issu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2006,8(2):84-94.
[21]Dimitris Mattheou.The Scientific Paradigm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A].Robert Cowen,Andreas M.Kazamias.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C].Dordrecht:Springer,2009.59-71.
[22][42]John Harriss.The Case for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e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J].World Development,2002,3(30):487-496.
[23]L.Richard Meeth.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A Matter of Definition[J].Change: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1978,10(7):10.
[25]Watson,K..Comparative Educational Research:The Need for Reconceptualisation and Fresh Insights[J].Compare,1999,29(3):234-248.
[26][29][英]贝磊.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跨学科性及非学科性[J].肖玉敏译.全球教育展望,2004,33(9):3-8.
[27][西班牙]何塞·加里多.比较教育概论[M].万秀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18.
[30]王长纯.当代国外教育家群简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115
[31][33][34]George Z.F.Bereday.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Methodology in Education,1964-1966[J].Comparative Education,1967,3(3):169-187.
[32][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M].姜智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35]朱旭东.论比较教育研究的跨学科性——比较教育亚学科群建构[J].教育学报,2011,7(4):46-53.
[36][德]Wolfgung Brezinka.教育目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成功:教育科学体系引论[M].彭正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37.
[37][英]卡尔·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242.
[38][英]迈克尔·吉本斯,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沈文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40]Smirnov,S.N..The Main Forms of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Modem Science[A].Z.Javurek,A.D.Ursul,J.Zeman.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he Systems Approach[C].Prague:Academia,1984.68-70.
欢迎关注《现代教育科学》(月刊)
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版:xdjykxgjyj